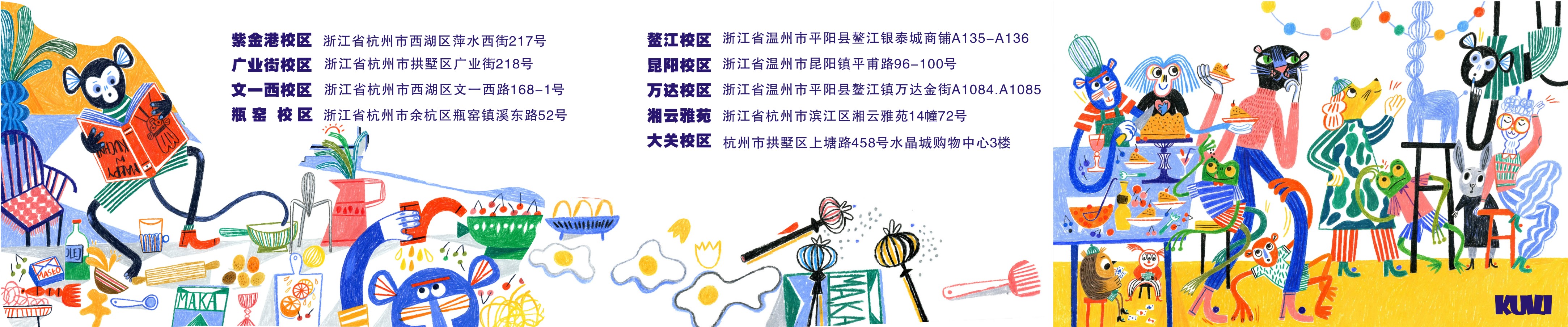陳丹青,平素一向保持短發,衣服的紐扣喜歡一直鎖到脖頸——一個也不落下。黑色褲子,黑色皮鞋。潔凈的臉龐,好大的眼睛,取來無框的眼鏡戴上,粲然一笑:這些年寫作,把眼睛搞壞了,這下我看清你了。舉止優雅,言語不驚,哪是報紙上白紙黑字、千篇一律、寫得分明的那個憤怒甚而偏激的人?媒體為奪眼球,有時難免簡單化,畫臉只畫半張,色彩只用一種。取其一點,不及其余,尚可接受,要不得的是取了筐來,把人往里裝,偏又不讓爭辯。陳丹青道:“各報的形容詞,也真看得我心驚肉跳。‘拂袖而去’,那要古人的寬袖這才拂得起來;‘拍案而起’,我與領導談辭職,彼此笑瞇瞇,誰也不紅臉,國中單位的情面禮數,大家應該知道的。”
《退步集續編》首印十萬冊,為了配合出版社的宣傳,陳丹青需要連軸轉,被他自嘲為:接客。
你莫看陳丹青歸國以來只是或黯然懷舊,或激憤發言,或批評城市,或笑談魯迅;一襲青衫,瀟灑走動,風光無限。你又怎么知道作為畫家的陳丹青,內心里有著怎樣的思量?他的手上雪藏和醞釀著怎樣的大作品?陳丹青終究不是做戲給“沉默的大多數”看的人。一個人坐在舞臺中央,燈光明晃晃照著,他不見人,人則皆可見他,此番場景哪是這個聰明人的所好!回到畫室僻靜一角,他最終揮舞的,是手中的畫筆,最終留世的,也許更會是他或舊或新的組畫。所以,陳丹青所言之“退步”,或者他“退步”的姿勢,套用老子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曰:
“退可退,非常退”,大約不錯。
關于清華辭職:“我只是逃開,同時叫罵幾句”
要說今日的讀者,知道陳丹青的,首先是因為“清華教授辭職”事件,其次是因為《退步集》和《退步集續編》這兩本書,再次恐怕才是作為畫過《西藏組畫》的畫家。連陳丹青也疑惑先前哪想到回國教書呢?結果辭職走掉,更不料此事演成社會話題,從此好像欠了前世的債,給輿論逼成“批評專業戶”。
自從到了高校教書,陳丹青和許多教授一樣,每到招生的季節,必須面對一疊厚厚的碩士生、博士生報考表格,上面填寫著考生的姓名、年齡、民族、政治面貌、學歷。其中最要緊的,是政治、外語科目的分數。都說要不拘一格降人才,陳丹青感嘆:一格一格,全是格呀!人的才氣、性情、素質,統統變成了表格數字,哪里可以看得出考生是怎樣一個人?
“普天之下,莫非體制。”陳丹青舉了一個例子:當年國學研究院招生,四川一位18歲考生錯過報名期限,獨來京城求見梁啟超與王國維,梁、王居然出見,略略問過來歷,梁就想要他,王則引他進里屋考高中語文數理,約一小時半。翌日電話招那學生,即請門房將行李搬入宿舍,上課如儀。1978年,陳丹青自己投考“文革”后中央美院第一屆油畫研究生時,他在外語考卷上寫下“我是知青,沒有上過學,不懂外語。”隨即交卷,離開考場。結果,那年陳丹青以外語零分、專業高分被錄取。
時間輪轉二十余年,英語和政治兩課考試的嚴格限定,使陳丹青四年招不到一個碩士生,他慨然奔走,以無果而終。2003年起意辭職,他說是性格使然,“我頂喜歡尼采一句話:‘服從?No!領導?No!Never’”另外他也覺得年過五十,望見六十,希望重新在畫布上撲騰。為此事,陳丹青小心躲著媒體,躊躇數月,終于還是被弄出了巨大的動靜來,直到2007年春上走成,辭職這一私人事件已經世間紛揚,讓他無處躲藏了。“我只是逃開,同時叫罵幾句,就像小時候在弄堂打架,打不過,一路逃一路叫罵,罵給自己聽聽,也罵給別的弱者聽聽……”社會上渲染他“退出游戲”的決定,使他在體制內的同行面前感到難為情,甚至愧疚。“體制內很多人認真教書,正派做人。在妥協和不妥協之間,他們很難,很辛苦,我理解他們,尊敬他們。”
關于上海:上海是很好的“啟蒙老師”
1970年,17歲的陳丹青開始輾轉贛南與蘇北農村插隊落戶。那時節,勾銷上海戶口幾乎是所有上海人的晴天霹靂。陳丹青茫然離開曾經打架、追逃、斗蟋蟀、爬屋頂的上海石門一路老弄堂。他早年的主題性創作《給毛主席寫信》,表現一群知青決意“扎根”農村的心意,而他內心卻和成千上萬知青一樣,盼望回城。
1982年赴紐約定居,2000年:回國在清華大學執教。去國十八年,戶口迂出上海則已經37年了。對上海這座城市,陳丹青說“我渾身上下都是‘上海因子’,雖然不確知那是什么。我的‘處世方式’里布滿了上海‘密碼’,因為‘布滿’,而且是‘密碼’,反倒難以舉證。”
也許舉這樣一個例子可以管窺陳丹青的“上海情結”。1993年陳丹青回國探親,第一件事就是想在上海街頭吃碗陽春面,卻怎么都沒找到。“我心里胃里登時沒著沒落地,多年夢想的回國劇情才剛開幕,這第一出戲豈不就得泡了湯亂了套了?”幸虧有善解人意的老板娘喔喲一笑:現在沒人吃陽春面啦,剛從外國回來吧?好,今天專門為你做一碗!而后,他騎上父親的“老坦克”自行車,摁著車鈴穿弄堂,故意吃幾個“彈簧屁股”,聽座下的小彈簧“咯吱咯吱”響。
“傷感主義并非僅指心頭的思緒,懷舊離不開‘物質’”。喜歡在掌燈時分漫步走過哪條好弄堂走進去游蕩的陳丹青,自稱“像個鬼”,看人家收回晾出的衣服,門開門關,聽弄堂外被隔離的市聲。陳丹青說,這是一個50多歲的人的懷舊,個人的一些情感,不能太當真。兒時老屋已經沒了,但“家”的感覺還在,“風吹過來,還是上海的風。”
“上海對我非常重要,它是偉大的啟蒙教師。”陳丹青說,他無法想象自己出生在別的地方。“上海使我與歐洲不隔,這是‘最大的影響’,可是直到我中年造訪倫敦巴黎這才明白。當然,‘油畫’是上海于我的影響中至關重要的一環。我想起我是上海人,同時,莫名其妙想起油畫。”
“來世投胎,我愿在上海,但不是今天的上海。”陳丹青指的是一個藝術的上海,“三十年代的上海豈止是中國文化的半壁江山,在亞洲也獨執牛耳。中國現代電影史、油畫史、音樂史、戲劇史、廣告史,和一部分文學史翻譯史出版史及所謂文化產業史,差不多就是‘上海史”。在陳丹青的印象里,尤其是從九十年代開始,文化的上海逐漸凋敗了。他認識的幾位文藝朋友在九十年代末興沖沖去上海闖,不久又回到北京。搞文藝的不愿進來了,在上海的人也不愿出去了。而他們那時候都愿意出去,知青一代畫家,有多少是從上海出去的?“這些年我招生的時候,很關心有沒有上海的學生,請他們舉手,結果幾乎沒有。”這使陳丹青感到悵然。
關于《西藏組畫》:未完成的誤讀之作
1980年1 0月,陳丹青的《西藏組畫》在中央美院研究生班畢業展上引起轟動,日后與羅中立的《父親》并稱為中國當代美術史的里程碑,逐漸變成一段神話。而在《西藏組畫》聲名大噪之際,陳丹青離開了中國。此后,他成為中國藝術青年遙遠的楷模。2000年,陳丹青回國任教,閃耀的光環使今天的公眾很難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在看過批評家努力建構《西藏組畫》的神話文字后,令人釋然的是,陳丹青對自己的歷史保持著隱忍、理性而誠實的態度。
“我畫西藏組畫時只想畫得和米勒一樣,追求我心目中法國式的現實主義。”陳丹青說,“我對西藏既不了解,也談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,當年我把西藏的視覺經驗當作法國繪畫的替代,那是一種故意的誤讀。歷史常被誤讀,西藏組畫被神話,也是出于誤讀吧。”
“作為影響,假如真有影響的話——《西藏組畫》是失敗的,至少是未完成的。我們因緣際會撞上時代,但沒有延續并展開當初的命題,構成堅實的文化脈絡,就像第五代導演個個背離了自己的初衷。我們全都來自斷層,沒有歐洲人的深厚背景與文化準備,九十年代的創作理應超越我們,我想,其中凡是不受影響的家伙,才真有出息,例如艾未未和劉曉東。
上世紀80年代的所有探索是真摯的,但都很粗淺,急就章,它填補了“文革”后的真空。我的《西藏組畫》實在太少了,一共七幅,算什么呢?居然至今還是談資,我有點驚訝,但不感到自豪。
當時我就清醒認識到這一層。1980年10月我畢業留校,1982年元月我就走了。”
關于文學:歸國七年出書五本
陳丹青的父親說,對丹青小時候的印象,就是他非常自信,送他去學游泳,還沒下水,他就覺得自己一定會游。陳丹青從小就喜歡游泳、音樂、文學、繪畫,但其實一開始根本沒有想到讓他學畫。陳丹青4歲那年,父親就被戴上了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,家里的書籍、畫冊被一掃而光。丹青難過得整天沒說一句話。父親勸他說“別難過,沒有畫冊臨摹,到公園、馬路去畫。”一次,父親在打掃衛生時,在垃圾箱里拾到一張撲克牌,背面是色彩濃重的油畫,原來這是一位僑居意大利的俄國著名畫家的杰作《意大利姑娘》,他馬上拿回家送給了兒子。丹青花了幾個星期臨摹,竟畫得栩栩如生。
父親這樣評價兒子:在繪畫時,丹青沒有畫高大全的人物;在寫文章時,丹青敢講真話
陳丹青說,他經歷了非常匱乏的時代,少年時無書可看,在圖書館“偷”得一本《牛虻》,如獲至寶。小學畢業后,他“突然遭遇魯迅”,那時,《魯迅全集》成了他唯一可看的書籍,卻也讓他可以全心全意地只讀一個人的著作。14歲時,他替“右派”父親寫申述狀,一點都不能出錯,于是學會了技巧。40歲時,畫畫的陳丹青不料自己也作起文章來了,而且一如畫畫般流暢和充滿快感。歸國七年來,陳丹青已出了五本書,《退步集》和《退步集續編》之前的三本是《紐約瑣記》、《陳丹青音樂筆記》和《多余的素材》。出第一本《紐約瑣記》時,出版社印了3500冊,擔心銷不掉。2005年出版的《退步集》,如今已是第十三次印刷,達到十一萬冊,并獲得第二屆“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”,且是獲獎的10本書中唯一的人文書。2007年4月出版的《退步集續編》,開印就是十萬冊,有媒體認為是第17屆全國書市“唯一亮點”。連陳丹青本人也詫異為什么會有這么多讀者了,“是我招惹還是在被招惹?是如今的言論空間稍許放寬,還是仍舊少得可憐?或許都是原因吧。”